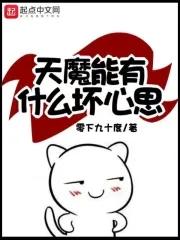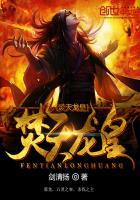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华娱:重生了,还逼我做渣男啊 > 第六百二十四章 死都不会接(第2页)
第六百二十四章 死都不会接(第2页)
“当然。”阿英代答,“只要你心里有波涛。”
“那……贫穷算不算一种‘忧’?”
老人听完问题,闭上眼,许久才开口:“贫穷让人苦,但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真正的‘忧’,是你明明苦着,却还想着让别人少受点苦。”
这句话被陈诺剪进了预告片,配以山间晨雾缭绕的画面,背景音乐是一段缓慢的手风琴独奏,旋律取自广西民谣《唱天谣》。
下午三点,阳光斜照进屋子。秦绍文忽然提起一件往事。
那是他瘫倒前的最后一堂公开课,主题是鲁迅的《故乡》。那天他站在讲台上,对学生说:“闰土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不是因为他懒,也不是因为命运不公,而是因为当他喊出‘老爷’那一刻,他放弃了自己与迅哥儿平等的灵魂。”
讲完这句话,他突然晕倒在讲台前。
“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他说,“学生们冲上来扶我,有人哭了。可我知道,真正该哭的,是我自己??因为我还没教会他们,如何守住内心的光。”
屋内一片寂静。连窗外叽喳的鸟鸣都仿佛停了下来。
陈诺没有打断,任摄像机继续运转。他知道,这不是回忆,是一次灵魂的剖白。
傍晚,一名十七岁的女孩翻山越岭赶来,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手抄本。她是附近村小的代课老师,也是秦绍文最早的“远程学生”之一。她说,自己当年差三分落榜师范,几乎放弃学业,是靠着反复听秦老师的录音撑下来的。
“我现在教三个年级的语文。”她红着眼眶说,“每次备课前,都会先听您讲一遍。”
秦绍文听后,久久无语。最后,他让阿英拿来一张纸,用左手极其艰难地写下一行字:
>**“教育不是火炬传递,而是星星相映??你照亮我,我照亮你,于是黑夜有了形状。”**
女孩接过纸条,跪坐在地,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夜,陈诺独自坐在院中,望着满天星斗。这里的夜空比怒江更清澈,银河如一条银色河流横贯苍穹。他想起达瓦和卓玛,想起扎西,想起洛桑,如今又遇见秦绍文。
这些人,都不被时代聚光灯照耀,却用自己的方式,在黑暗中凿出了光。
手机震动,吉克阿木发来消息:
“《听见光》在山谷电影节获‘金穗奖’最佳纪录片。扎西老师已抵达丽江,明天就能见面。”
陈诺回复:“告诉他,我这就去接他。顺便??带上一份特别礼物。”
第二天一早,他启程返回云南。临行前,秦绍文让他停下。
老人费力地抬起手,指向墙上挂着的一幅学生送的毛笔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然后,他看着陈诺,一字一顿地说:“下一个故事,我不希望你只拍‘牺牲’。你要拍‘传承’。那些接过我们手中火种的人,才是真正的光。”
陈诺深深鞠躬:“我会的。”
七日后,丽江古城外,玉龙雪山巍峨耸立。山谷电影节开幕式在一片草甸举行,四周彩旗飘扬,各国影人云集。舞台中央,竖立着一块巨大的投影幕布,上面滚动播放着本届参展影片海报。
《听见光》位列首推。
当主持人宣布“请主创团队登台”时,全场掌声雷动。陈诺牵着扎西的手走上舞台。这位盲人少年穿着整洁的藏袍,脸上带着腼腆却坚定的笑容。他看不见观众,但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温度与善意。
手语翻译站在侧台,将主持人的话实时传达给他。
“扎西同学,你现在最想对世界说什么?”
扎西沉默片刻,随后举起双手,开始用手语表达:
>“我不是特殊。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