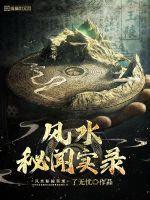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七零年代小知青 > 工分(第2页)
工分(第2页)
“我叫李红英,57年1月份的,高中读了一年。”李红英是京市的四个知青里唯一的那位女同志,说话大气直爽。
等他们继续说下去,天都得黑了。秦满仓拉着牛起来,牵好绳,催促道:“你们快把东西放上去,自己也上去坐稳,出发了。”
“哎哎,好。”
阮杨个子不高,但力气不小,带着大堆小堆东西很快就上车安顿好,还帮着老乡李红英拉了一把,坐好了,就有闲情聊着聊那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几颗什锦糖塞给秦满仓,打听道:
“大爷您怎么称呼啊?咱们这到大队要多久啊,大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大队的情况?”
杨家彤看着她舅黝黑的皮肤粗糙的面庞,忍俊不禁,是很显老哈。
把草帽盖在头上,这牛车板宽敞,她寻了个舒服的姿势坐着。
秦满仓听到大爷这称呼面不改色,从善如流地接过糖装进胸前口袋,道:“我姓秦。从这儿到大队五公里远,牛车走得慢一点,得一个多小时近两小时。”
“队里还有五个知青,我们大队的知青院建得不错,住得肯定比你们城里宽敞,院里还有菜地,你们下了工可以自己种些菜和粮食吃。”
“今儿你们到得晚,明天给你们一天修整的时间,后天开始就得跟着大队的安排去下地干活了,以后每天都要上工,就跟你们城里的工厂一样,要是身体不舒服或是别的什么原来来不了,得找大队长或者别的大队干部们请假。”
车上三人都仔细听着,阮杨听完继续问道:“我们刚到,粮食怎么解决?”
虽然他以防万一,到县里时去买了些,但就那么点,能够吃几天啊?
“你们知青有补贴,大队会先给你们发两个月的粮食。好好上工,马上就夏收了,到时候也能分点粮食,不够吃到秋收,那你们就得自己花钱去买一些,或者向大队借些粮食记账。”
才两个月的粮食,李红英心里叹息一声。
只恨自己生得晚,要是早几年下乡,还能得两百块的安置费。
不过她不知道的是,以前有安置费的时候,大队是没有专门给知青安排房子住和不给粮食的,后来安置费没了,只是换成让大队给建宿舍且分粮食了。
都是一样的结果。
“大爷,咱们大队现在的收成怎么样啊?能人人都吃饱肚子吗?”阮杨嘻嘻哈哈地问道。
秦满仓瞅他一眼,直白道:“只要你努力上工,就饿不死。”
“我肯定努力上工,别看我人不高,力气可不小,不就是种地嘛,我肯定行。”
阮杨头一回到乡下来,还没经过生活的毒打,没把种地的艰难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不过是拿着锄头挖地,多简单点事儿。
另一个,只要能填饱肚子,种地就算再难他也得克服。很多时候他深深地怀疑,自己长不高就是因为没吃饱饭。
李红英也对着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有手就能创造粮食,这可比城里好一些,城里固定的那些供应,你没得工作,一个月再怎么办也只能得到那些粮食。
她家条件不太好,亲妈常年卧病在床,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杨家重担全在她爸一个人身上,想吃饱和吃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找不到工作的前提下,她对下乡的抵触不大,又分不到国营农场,现在就希望分到个富裕一些的大队,到时候能帮衬家里。
她找胡同里下乡的哥哥姐姐们打听过,在大队,每天挣的就是公分,分粮时要看它,年底分钱时也看它,穷的大队一个工分几分钱,顶顶富裕的大队一个工分能值一毛一、一毛二。
且富裕的大队粮食多,光是人口粮就能多分一些。
她是这么想的,自然也就问出口了,“大爷,咱们大队去年的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啊?”
秦满仓笑呵呵的,心想这越往后来的知青对他们乡下了解的还多一些,地方都还没到就已经知道工分这东西了,他回道:
“咱们大队去年收成不错,交的公粮多,算下来一个工分5分7厘,你们知青点能耐的,去年一年除去粮食,还能有六十多块钱的分红呢。”
李红英这下心里有底了,看来这个大队的情况不算太差,年底多少也能给家里寄去些东西。
杨家彤也盘算起来,她这辈子长这么大,就没经手过多少钱,现在还是因为走之前她妈给了三十,存款才终于上了二位数。
她力气大,上辈子更恶劣艰难的环境都待过,这儿绿水青山的环境好多了。她早日适应下来,每天多挣工分,年底分到手的分红肯定不少,再加上她爸妈每个月还会给的补贴,应该能过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