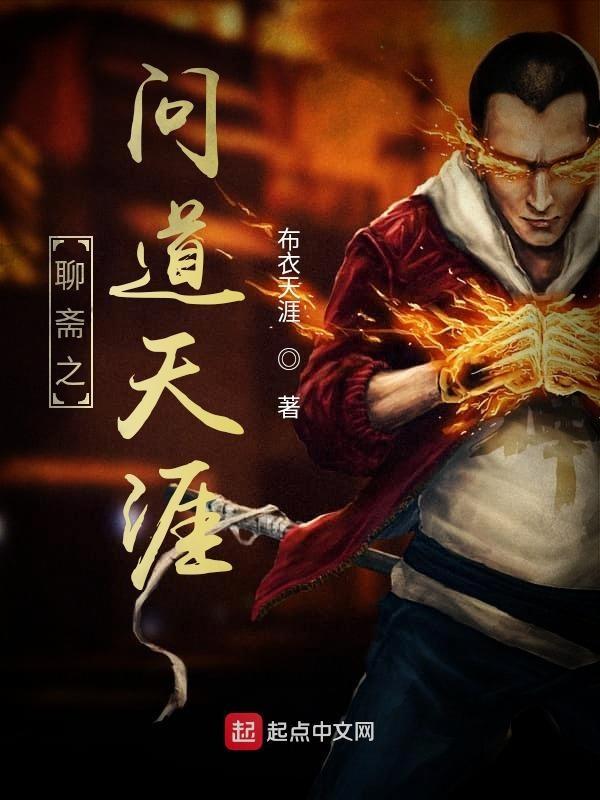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解春衫 > 第154章 终极抹杀(第1页)
第154章 终极抹杀(第1页)
陆铭章顺着戴缨的话,问第二件好事是什么。
“爷你坐,我去去就来。”戴缨起身,走出屋外,不知做什么去了。
此时天色暗了下来,窗纱上映着淡蓝的光,屋里的光线更暗,陆铭章起身点亮灯烛。
再看了眼冷清的屋室周围,静地让他不适应,急于寻找她的身影和声音,于是走到门首,往月洞门看去,没有人,心里蓦地有些慌乱,正待往院外走去,就听到细碎的脚步声。
连他自己都没发觉,在听到那熟悉而轻快的脚步声时,全身的紧绷松散下。。。。。。
夜深了,江南的春寒仍带着湿意,沁入骨髓。谢?坐在院中石凳上,手中那件破旧春衫已补了七处补丁,针脚细密如初雪落纸,无声无息。她指尖微颤,却不肯停下??这衣裳是戴缨生前亲手裁的,粗布靛染,袖口绣着一朵歪斜的腊梅,说是“不像样才好,像样了就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了”。
归雁站在廊下,望着她背影,忽然觉得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妇,竟与三十年前紫宸殿上那个白衣红袍的身影重叠起来。一样的孤绝,一样的坚定,只是如今的光不再锋利如剑,而是温润似水,缓缓流淌在岁月沟壑之间。
“你真不打算回京?”归雁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梦。
谢?没抬头,只将线尾咬断,轻轻抚平衣襟:“京城里有春衫卫改的国民平等署,有女子学院,有科举放榜时万人空巷的盛况。那里不需要我了。”
“可岭南的事……”
“我知道。”她放下针线,抬眼望向天际,“乳母之子,陈厉义子,名叫周砚舟。藏身于雷州府外一座盐场,化名林守业,经营私盐多年,暗中仍与残余东厂势力勾连。他手里还握着一份名单??当年参与构陷谢家的官员后代,至今仍在朝中任职者十七人。”
归雁心头一紧:“你要揭出来?”
“不。”谢?摇头,“揭出来只会引发动荡。新政十年,根基尚浅,若掀起血雨腥风,百姓又要为权斗买单。我要去见他。”
“你一个人?”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她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一枚银簪,簪头刻着极小的“春”字,“只要还有人记得这根簪子的意义,我就有千军万马。”
次日清晨,谢?背起一只布囊,内装几件换洗衣物、一本《女诫新解》、半块干饼和那根银簪。她没有惊动镇上学堂的孩子们,只在门楣上留下一张纸条:“我去寻一段旧账,归来时带新梅。”
归雁一路送至渡口。江雾弥漫,乌篷船静静停泊,艄公戴着斗笠,默然等候。
“你信不信他会认你?”归雁问。
“我不知道。”谢?踏上船板,回眸一笑,“但我相信,一个母亲被活活逼死的人,不会完全忘记痛是什么滋味。”
船行七日,穿湘江,过灵渠,入珠江,终抵雷州。此地滨海,风咸浪浊,盐田如镜,反射出刺目的白光。百姓面黄肌瘦,妇女裹头巾劳作于烈日之下,孩童赤脚奔跑在碱土之上,口中哼的却是《春衫诏》第三条:“凡民皆有求学之权,不论男女贫富。”
谢?在小镇客栈住下,自称是游方医姑,替人针灸疗疾。不过三日,便有十几个妇人排队求诊,有人抱着咳血的孩子,有人扶着瘫痪的老母。她用药简而准,言语温和,渐渐赢得信任。
第五日黄昏,一名少年送来一封信,署名无字,仅附一片晒干的腊梅叶。
她认得那叶子??三十年前,戴缨曾用这种腊梅叶夹在书信里,作为紧急联络的暗记。
当晚子时,谢?依约前往城外废弃的观音庙。月色惨白,照见残垣断壁间一人负手而立,身形瘦削,披黑袍,戴竹笠。
“你来了。”那人声音沙哑,“我以为你会带兵来抓我。”
“你是周砚舟?”谢?站在三步之外,不动。
“曾是。”他缓缓摘下竹笠,露出一张布满疤痕的脸,“现在我是林守业,雷州最大私盐贩子,也是朝廷通缉多年的钦犯。你说,我该不该杀你?”
谢?静静看着他:“你母亲姓赵,是我父亲贴身侍女,自幼照顾我饮食起居。你六岁那年发高烧,是我娘亲自煎药喂你,整夜守在床边。后来她为你求了个文书差事,才让你进了户部当小吏。这些,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