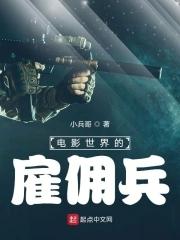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华娱:重生了,还逼我做渣男啊 > 第六百二十七章 我有一壶酒(第2页)
第六百二十七章 我有一壶酒(第2页)
>**“他曾说,最怕的是荣誉让他照不到孩子的眼睛。
>若真要致敬,请把这笔经费拨给西部乡村学校,建一百间图书室。
>书名统一刻上:‘秦绍文微光计划’。”**
消息传出,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出版社免费捐书,物流公司义务运输,志愿者自发前往偏远地区搭建书屋。短短一周,第一批三十间图书室落成,孩子们抱着新书坐在地板上阅读的照片传遍网络。
而这一切,秦绍文仍不知情。
他的身体已虚弱到几乎无法说话。每天清晨,他靠阿英搀扶才能坐起片刻,听广播、批作业、口述回信。咳嗽日益频繁,有时整晚都无法入睡。医生来看过,摇头说:“最多还有一个月。”
小岩得知后,连夜翻山越岭赶来,背着一袋自家种的土豆,脸上全是汗水与泥土。他冲进屋里,扑到床前,一声“老师”还没喊出口,就嚎啕大哭。
秦绍文努力扯出笑容:“傻孩子……哭什么?你不是说要考大学吗?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小岩抽泣着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成绩单:“数学……九十二分……全班第一!”
秦绍文看着那分数,眼里闪过一丝光亮,轻轻说了句:“好。”
他又问:“作文呢?”
小岩低头:“写了您……题目叫《我的光》。”
秦绍文笑了:“念给我听听。”
小岩清清嗓子,声音颤抖却坚定:
>“我的老师躺在床上二十年,连路都不能走。可他说的话,比谁都走得远。
>他教会我,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认命。
>他让我妈回来了,让我敢做梦。
>以前我觉得光在天上,现在我知道,光在人心。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哪怕倒下,也要发声。”
>
念完,屋里一片寂静。
秦绍文久久未语,最后抬起枯瘦的手,轻轻摸了摸小岩的头:“你已经……是了。”
当晚,小岩睡在堂屋的竹席上。深夜,他听见里屋传来低低的吟唱声,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慢板,断断续续,却无比执着。他悄悄起身,趴在门缝往外看??阿英正握着录音笔,父亲闭着眼,嘴唇微动,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那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他忽然明白,老师不是在唱歌,是在告别。
四月中旬,山花凋谢,新叶初生。
林晚专程从贵州赶来,带着三十八个学生的合影、一封扎西写来的信,还有一本厚厚的学生作文集。她跪坐在床前,泪流满面:“老师,我没辜负您。他们都考出去了……有两个报了师范。”
秦绍文看着照片,一个一个辨认名字,低声念出他们的未来志向。听到扎西考上县中重点班,立志当语文老师时,他嘴角扬起,轻声道:“种子……发芽了。”
林晚拿出作文集:“学生们都说,想让您再讲一课。”
秦绍文沉默片刻,说:“讲《送东阳马生序》吧。”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纸洒进来。秦绍文靠在床上,精神竟难得地好了些。他让阿英架好录音设备,又让林晚打开作文集第一页。
他缓缓开口,声音微弱却清晰: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
他讲宋濂年少时抄书苦读,讲寒冬砚台结冰,手指冻僵仍不停笔;讲他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足肤皲裂而不知;讲他寄居旅店,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
“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他念完这句,喘息良久,才继续,“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岂他人之过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林晚、阿英和小岩:“你们觉得,现在的孩子还缺什么?”
没人回答。
“不是书,不是饭,不是衣服。”他说,“是那种‘宁愿挨饿也要读书’的心气。”
林晚红了眼眶:“可条件好了,人心就散了。”
“所以更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秦绍文轻声说,“富贵未必要骄,贫贱不必自弃。真正的差距,从来不在起点,而在是否愿意一直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