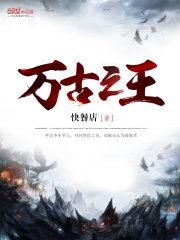笔趣阁中文>权臣成双 又生 > 8090(第19页)
8090(第19页)
该段河道的管理权分属二省,但漕运调度权归中央,地方利益与漕务冲突时无协调机制是一处弊病,其次因《工律》未有对征调比例的限制,导致地方官员为完成政令而无度征役。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律法失修的现状。
林佩说话一向有理有据,这种水面之下冰山静悬的气度亦是威慑。
董颢张了张口,又把话吞回肚子里。
林佩道:“今日叫大家来也是想群策群力,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他的话音一落,堂中就安静了下来。
尧恩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董颢不停地翻案卷,眼珠左右摆动。
万怀起身道:“林相,二位尚书,下官作为旁观者有些愚见,说出来就当是抛砖引玉。”
林佩道:“你对钱粮运转了如指掌,如何能说是旁观者,但说无妨。”
万怀道:“那下官就说了,这些案子之所以会发生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一个是权责不清,一个是运法不当。”
尧恩道:“万侍郎,何谓权责不清?”
万怀道:“户部、工部的清吏司每年把任务摊派下去,漕运司盯着地方完成,结果一定是各地官员各自为政。陆相当年在淞江任知府是连续两年都完成了转运百万石的重任,但不能让我朝官员一个个都像陆相那样干,运多少,怎么运,征召多少人工,占用多久农时,必须由部院、漕运使和地方官员一同制定方案,层层追责,交叉监督,这样才能避免乱象。”
尧恩道:“你说的不无道理。”
董颢道:“那什么叫运法不当呢?”
万怀道:“不是下官班门弄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按现行的办法,转运钱粮须由地方征调劳役或船只将漕粮从产地运送到指定的中转港口或仓库然后一站一站往下运,每次交接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导致效率低下,运力不足。”
董颢道:“你说的是实情,陆相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自他主张官私合营以来,许多地方效法他曾经的做法,开始雇佣商帮承担部分远途运输任务,这不成文的方法叫兑运。
林佩道:“既然支运能变成兑运,是否可以让各都督府出一部分士兵来运送漕粮,设专用河道从江南直抵北京,以最快速度解决前线军粮短缺问题,称为直运。”
董颢道:“或许……可以一试。”
万怀道:“诚如是,三种方法搭配使用,各地协同合作,便可以大大提高漕运的效率。”
清风过堂,带来一阵兰花香。
林佩看看万怀,眼中流露出几分欣赏的神色。
昔年一见上司就脸红的书生,如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万怀提出的这两个原因,当堂两位尚书心中定然也清楚,之所以不说,董颢是不愿意把饼拿到台面上来分,尧恩是不想当着外人的面说内心想法,这时候就正需要一个像万怀这样的人捅破窗户纸——朝廷是为一时的安定才容忍工部治漕的现状,如今北方初定,重修漕运法这件事无关公私,势在必行。
众人讨论的时候,温迎在一旁打理那幅《明皇幸蜀图》。
林佩道:“温迎,你觉得万侍郎说得可有道理?”
温迎放下掸子,笑道:“有理。”
董颢道:“林相,我插一句,陆相原来不是定下过‘一江,两河,三道,四行’的方略吗?现在施行的好好的,为什么又要改动呢?”
林佩道:“董尚书应当知道我不是个喜欢乱改动的人,‘一江,两河,三道,四行’的方略仍继续施行,我们现在做的只是为了让这个方略有法可依,更加完善。”
董颢道:“治漕的干系非同一般,陆相那儿明年还要远征乌兰,一百万石军粮的担子压在工部,如果中途因为这趟修订律令出了什么差错,谁来担责?”
第86章家书
“出了差错自然是我们一起担责。”温迎往外甩了一下掸子,“但现在似乎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必如此戒备吧。”
“虽如此……”董颢道,“唉,林相,下官也是实话实说,若有冒犯还望见谅。”
林佩笑了笑:“你提到平辽总督府的军需,我正要说此事。”
董颢道:“此话怎讲呢?”
“去岁你也说过漕运运力吃紧,若当下不加以整治,万一陆相远征乌兰的时候天灾不断怎么办?”林佩道,“比起那个时候的大风大浪,我宁愿现在动点沙土筑牢堤坝。”
董颢一时语塞,实在辩驳不过。
铜漏滴着水。
林佩等了片刻,见几人无异议,敲定此事。
今春将由刑部牵头、工部各漕运司和地方州县协作,对《大阜律》中的漕运法进行新一轮的修订,于夏季正式实施。